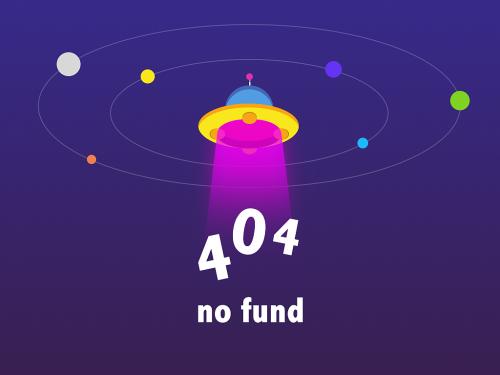文娱动态
民国律师公会的自治困境探析
日期:2014-05-26 作者:杨立民
所谓的行业自治,在法理意义上是指社会组织的一种自我管理和治理的行为和状态。行业自治不仅体现了社会团体的主体性价值,还是社会民主进程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现代意义上的律师行业自治是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律师自治组织对律师的行业准入、执业规范、业务培训、执业纪律及执业惩戒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种行业管理方式。
律师公会是民国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法律近代化的结果。民国律师公会拥有一定的自治权,比如有权可以制定自治规范,享有行业准入审查权,可对执业律师提请惩戒,对执业律师是否可以兼营商业有决定权。另外,律师公会还通过各种努力来维护执业律师的权益和信誉,并广泛参与到民生救助、民主推动、民族解放等各种社会活动中。但是,律师公会自治权的获得并非一帆风顺,其自治过程也面临着种种侵扰和困境。
困境一:国家管控
律师制度是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设计,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国家在赋予律师公会自治权的同时,一般也会加强对它的监管。在民国时期,对律师公会的监管最初是由司法机关来负责,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民间团体的管制。
(一)司法机关的监管
根据1912年《律师暂行章程》的规定,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门对律师公会有以下监控权:
1、检察长的监督权。地方检察长对本地所设立之律师公会享有监督权,该地方检察长可以随时出席律师总会及常任评议员的会议。律师公会应将会长、副会长和常任评议员的选举情况、常任评议员会议的开会时间和地点、提议决议事项等各种会议详情随时报告给该地方检察长,地方检察长接受报告后即通过高等检察长报告于中央司法总长。
2、公会章程的批准权。公会自治规范的制定权是律师公会自治的重要表现之一,民国时期的律师公会享有章程的制定权。但是,律师公会议定的章程需由地方检察长经高等检察长呈请司法总长批准,这与《律师章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会议有效性的决定权。律师公会或常任评议员会有违反法令及律师公会会则者,司法总长或高等检察长得宣示其决议无效或停止其会议。
1941年的《律师法》对律师公会的监控进一步加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的监督被进一步确定为“直接”监督。会员增加的名册及入会、退会的情况被规定为向地方首席检察官报告的事项。由原来的检察官单独监督增加为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共同监督,即地方首席检察官接到律师公会的报告后应通过高等检察长会同高等法院院长共同呈报司法行政部。
(二)地方政府的监控
抗战前,国民政府对律师公会的监控主要是由中央司法行政部和地方各级检察长来主导,地方政府对律师公会没有法定的控制权。但随着抗战的爆发,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件来逐步加强各级政府对包括律师公会在内的民间社团的控制。1942年2月3日,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颁布的《人民团体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工作实施纲要》规划了抗战时期人民团体的中心工作,试图通过非常时期利用非常手段加强对民间社团的控制。1942年2月10日公布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人民团体的主管机关依次为:中央社会部、省社会处(未设社会处之省为民政厅;院辖市为社会局)、县市政府。人民团体受这些机关的指挥监督。1945年的《律师法》更是从立法形式上规定了律师公会的主管官署在中央为社会部,在地方为省市县社会行政主管机关。为了避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管辖冲突,该法同时规定“其目的事业应受司法行政部及所在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之指挥”。
在1940年司法院的第2096号解释中,县政府对律师公会自无监督指挥权。但《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颁布后,司法院在第2577号解释中确定了县级政府对律师公会的监管权。
(三)社会参与的严格限制
国民政府主要是通过特殊立法,以限定性列举的方式将律师公会的社会参与权限制在法定界限内。1927 年《律师章程》的第32条规定:“律师公会于下列事项外不得提议决议:1、法律命令及律师公会会则所规定之事项;2、司法部长或法院所咨询之事项;3、关于修改或司法事务或律师共同之利害关系建议于司法部长之事项。”其后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法》也沿袭了这些规定,并逐步加强。
(四)监管权的掣肘
律师公会对执业律师拥有一定的监管权,这是律师公会自治的重要表现。律师公会对律师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律师违背律师公会章程的处分上,尤其是对律师职业道德和行业纪律的监管。如果律师违反纪律和道德比较严重,律师公会可依据章程规定给予退会处分。如果律师有应受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则直接由司法机关向律师惩戒机关提请惩戒。这是一种行业自治和国家监控双重运行的体制。
但是,民国律师公会的监管权受到种种掣肘,其根据章程所实施的监管行为是否有效决定于国家。比如,在“上海律师公会对郑毓秀的退会处分案”中,江苏高检宣布上海律师公会的处分无效,律师惩戒委员会和司法行政部均支持江苏高检的决定。这就导致上海律师公会对会员的处分权无法实现。后来,司法机关直接废除了律师公会开除会员的权力。
国家既然将对律师的监管等自治权赋予律师自治组织,那么也就需要相应地加强对律师自治组织的监管和限制,这在现代民主国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民国政府对律师公会的管制不是为了防止其滥用自治权,而是为了对律师公会进行政治控制。这种政治控制是与国民党对民间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党化控制政策分不开的。
困境二:党化控制
1912年律师制度确立之后,因为北洋政府的党派属性不是很明显,所以律师公会在这一时期并未受政党的控制。为了防止革命思想的影响,北洋政府还一直在法官、律师等司法群体中实行“去党化”。但是,1927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之后,在“以党治国”的统治理念下,包括律师公会在内的民间社会团体逐步沦为其操控的对象。
(一)通过对律师公会的改组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以上海律师公会的改组为例。1927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开始对上海实施全面控制。1927年4月2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致函上海律师公会,指出该公会原有职员任期已满,应“选出了解党治之律师数人,经本党部及政治分会认可,担任改组委员会负责起草律师公会章程,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同时由改组委员会接管律师公会,在新公会未改组成立以前代行其所有职权。”4月29日,改组上海律师公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市党部圈定改组委员名单,推举互选五人为常务委员。
在改组过程中,国民党自始至终都在施加影响。在上海律师公会春季大会召开期间,国民党上海党部一再要求上海律师公会要将大会的详情呈报上来。改组委员会的委员需经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的认可方能担任。为保证改组活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就改组委员会的组成及改组活动的进行提出了两个原则:(甲) 律师委员会,应具热心组织;(乙)对于建议案,应以少数人绝对服从多数人。”并威胁“设有阳奉阴违,故意捣乱者,则市党部当严重取缔。”
通过这次改组活动,国民党实现了对上海律师公会的控制,律师公会的各项活动也开始纳入到国民党的社会控制之中。大批律师在公会改组后竞相加入国民党,具有国民党党籍的会员对公会事务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大。律师公会开会时也要在会前履行朗读“总理遗嘱”等国民党会议的仪式。
(二)业务“指导”和组织领导
1927年后,为了加强对民众运动的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设立民众指导委员会,以指导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1930年1月,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的《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国民党对人民团体的扶植和指导地位。2月1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制定公布了《人民团体与党部来往公文程式》,确定了人民团体与各级党部的上下级关系。1930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组织程序》以及《人民团体组织许可证书颁发通则》,规定了国民党对民间团体的组织模式和组建程序进行监控。1933年2月9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指导人民团体改组办法》以及《各地高级党部指导人民团体权限划分办法》,再次强调了各级党部需监督主导各人民团体依照新颁布的法律进行改组。
(三)杀一儆百
如果律师公会对国民党的管控稍有触犯,国民党便会通过惩处律师公会中的国民党党员的方式来以示警戒。在1932年的“李时蕊被控案”中,我们看到国民党将本党的各种仪式强加给律师公会遵行,并以党纪代替国法,以党权代行国权。
国民党之所以如此想治李时蕊的罪,其真正原因是李时蕊在上海律师公会中热衷于民生公益和抗日救国等政治活动。他不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团体,而且还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作为国民党党员和上海律师公会主要负责人,李时蕊应这些行为大大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容忍的范围。所以,给予开除党籍、吊销律师证书以及秘密通缉等处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国民政府时期对民间团体和民众运动实行国民党指导和政府监督的双重运行模式,其对律师公会的控制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制定方案、国家进行立法的形式来实现。
困境三:“流会”现象
律师公会最高的权力机关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分定期大会与临时大会两种形式。大会以参会人数过半为有效,所议事项也以到会会员过半通过为有效。但是,律师是一个自由职业,律师们多在自己所属的事务所开展业务活动,他们参与会务的积极性并不高。会员大会的“流会”现象很严重,很多重大决议无法得到表决。
以上海律师公会为例。据《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记载,1921年至1926年间,上海律师公会共召开了15次会员大会(包括定期、补开、续开),其中有14次因与会人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改成“谈话会”。比如,1921年5月,上海律师公会召开春季大会,讨论派遣代表参加中华民国律师协会、无领事裁判权国家律师加入律师公会、陪审制度改革等议题。因198名会员中仅有59名到会,最后大会不得不改为了“谈话会”。在该年11月的秋季会员大会中,201名会员只有43人到会,只好临时决定三周后重开。而12月18日大会续开时,到会人数更少,只有38人。在1925年的春季改选大会上,先后到会的会员有77人,超过总人数153人的一半,符合会则的过半规定。但是,期间有8人因等的不耐烦而离席,以至于表决时只有69名会员,大会表决的合法性便产生了争议。在假定满足开会条件后,本次大会决议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会员大会召开的法定人数由过半数规定改为满三分之一即可召开。
但是,这一改变并未解决流会问题。1926年4月,上海律师公会召开春季会员大会,讨论收回会审公廨等议题。160名会员只有47人到会,大会只好再次改为谈话会。1927年改组上海律师公会时,到会签到的会员仅67人,不满法定开会人数。1936年4月,在召集的30次会员大会中,有20次因到会人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
主持日常事务的常任评议员会议相对比较容易召集,基本上可定期开会,但流会现象也时有发生。即使将每月两次的常任评议员会议减为每月一次后,情况也没有得到较大改善。
“流会”现象在其他律师公会中也均有发生。北京律师公会多次出现大会流会的情况,以至于在1918年发生了该公会会长邓镕自己解除自己的会长职务的事件。
作为律师公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会员大会常常因“流会”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律师公会自治权的行使,并损害了律师公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因为流会,新闻媒体在报道律师公会的会议情况时,所使用标题常为“律师公会谈话会记”、“律师公会开大会又未成”等。
困境四:时局混乱
民国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党国统治,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不一而足。在这样的执业环境中,律师公会不仅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还要尽力保护执业律师免受时局的过度侵害,同时还担负起匡扶社会正义和推动民族独立的责任。
比如,民国律师公会通过建立贫民法律辅助会来向贫民提供法律援助,设法保障和改善在押犯人的生存条件,推动冤狱国家赔偿的立法等。律师公会在创设之初便将收回国家的法权作为自己的民族使命。上海律师公会始终将废除殖民者的领事裁判权作为工作重心。为了收回上海租界的法权,上海律师公会积极组织各项活动,并不惜屈从党权。抗战爆发后,律师公会又冲破种种束缚,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上海律师公会召集的各种会议活动中,与“救亡”有关的议题占据了绝大多数。上海律师公会还决定本会执业律师不得与日本律师合作,不得为日本民众提供法律服务。
在现代民主国家,律师公会除了制约国家权力,实现自我治理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民国律师公会所承受的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其自治功能的正常发挥。●
(作者为复旦大学法学院12级博士研究生)